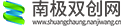在中国传统村落的版图上,一座七百多年的村庄应该算比较年轻吧?在海上丝绸文化熠熠生辉的泉州里,一座偏安一隅,四面都是山的盆谷地貌的村庄,放进有四百二十多公里海岸线的泉州地理格局里,是不是显得突兀?在以产业振兴乡村经济的新时代,一个世代以农耕为主,除了添加些山林收获,又几无其他产业的村庄,又会如何过上幸福生活呢?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安章村就是这样的,似乎单薄得让人不敢深想。可初见安章时,我的心就被钳住了。极目,天幕湛蓝如洗,几片白云停泊在村庄的上空。阳光下,群山环抱,绿意莽莽,稻田泱泱;两条醒目的路旁钉着音符状的黑色木屋,偶有车辆过境,旋即没入远方。
我们是傍晚时挺进住地的,简单拾掇后,暮色已苍苍。晚饭后,我们去村中仅有的小店采购,还来不及上山,天忽微雨。我扛着一箱矿泉水走在前,孩子们走在后。当我们正全神贯注于脚下的土路时,背后传来了“不要上去,很危险”的喊声。
回头一望,夜色中,一栋一字形排开的双层木屋亮着一团光,对着上山的小路。在二楼的廊道上,一位苍颜白发的老人正在挥手示意,他重复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我连忙答道,我们就住在山上的小屋里。这时,他又大声叮嘱,路滑,要小心。
翌日,我们竟成了村中的头条新闻。路遇村人时,他们总投以浅浅一笑。待你和他们打招呼后,他们总能不约而同地说出“你们就是昨天住在山上的”之类的话来,之后便是一番对来历的问询和嘘寒问暖。瞧着那一张张似乎熟悉的脸,原先心中被猎奇的感觉早消散在山风之中。安章,难道我是回来了吗?
与我们不约而至安章的还有台风卢碧。它自湛江发轫,穿过台湾海峡,一路向东北而去。安章多少受了影响,一连数日,雨水大作。这山村的夜和竹林一同环绕着木屋,蚊子和小飞蛾频频来挤占一室的温暖,肆意飞动的声响叠着屋外的雨声此起彼伏。难道它们都不会困倦吗?
你听,那瓦片上撒豆瓣般的雨点声,唰地一下子就摊开,不一会儿便如小珠落玉盘似的嘈嘈切切了。你还在静听时,它们又从瓦片的沟槽里溜到屋檐边,接连不断地砸在屋后的水沟里,哗哗交响。安章的夜雨啊,你是要用这种方式聊表欢迎吗?还是担心异乡的我们无法入睡,特地奏响一首长长的安眠曲呢?
雨把夜下得越来越深,我在床上谛听一室的宁静。屋檐上的雨水唰唰啦啦地翻滚,屋后的水沟里间或传来流水划动的声响。我蓦然想起同事曾说的清理水沟之事,赶紧下床,寻个竹斗笠和一把锄头,从大厅边的小门走进雨夜。
果不其然,水沟被堵住了,在一个屋角的拐角处堆满水,脚一踩,水直逼膝盖。我顺着流水的方向拖着锄头往外拉,走走停停,勾起杂物淤泥压成小垛,反反复复忙活半个多小时,终听见流水畅快向前纵声歌唱。我想,明天一定要带孩子们再打理下水沟,让他们好好地感受城市之外的生活。
听雨声,好入眠。一夜了无痕,朝日早在虫鸣和鸟啼声中欢腾。提起木插销,拉开木窗,窗外的翠绿向我扑来。那些经过雨洗礼的竹子像涤去纤尘,从头到脚都是青春的模样。好不容易除好草的埕被雨水倾情灌溉,残存的草根大有破土再出之势。我在想,兴许有的草根就在泥土中醉生梦死了,而那些正在潜滋暗长的,是要悄悄地铺成一地细小的绿,和微风轻拂的竹尖照个面,然后在我回望的某个时刻,给我一个假意叫苦的惊喜吧。这是雨和它们的暗语吗?
饱餐之后,我顺势喊孩子们一起干活。他们从埕边寻来一个老旧的竹簸箕,我将垃圾填装进去,他们抓起簸箕的手柄正准备往外运。“啪”的一声,手柄断开,簸箕碎裂成两半,一半垃圾散落在地,孩子们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见状,我便叫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过了好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出来。半腔怒气来袭,我折回工具房找他们。只见他们正东翻西找,仍未有决断。于是,我指了一个压在床下的编织袋,让他们拉出来。埕边的垃圾堆渐见丰满。水沟边的路几经踩踏已泥泞不堪,孩子们从屋角将垃圾搬出时,一不小心又倾倒一地。对着一地狼藉的污物,他们犹豫着如何装回去。我双手一掐,把部分垃圾拨回编织袋上面。紧接着,他们依葫芦画瓢,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
一个多小时的水沟清理和垃圾搬运工作后,我们都是一身泥水。冲洗污垢,还一身清洁。听着他们愉悦的声音,看着他们脸上绽开的花朵,我想这样的劳动终会在他们的心田里扎根,成为一份有力量的生命记忆。
半日劳动半日闲,也许今晚就等着雨来梦中告别吧。不知几时,雨声过后,阵阵蛙声和其他虫鸣声奏起,心头的安静随之落下,只许一阵风穿窗而入,吹下夜的温度,让人蜷在被窝里一宿到天明。
雨终于被台风带走,局促一室之内的心早按捺不住了,得赶紧下山,到村中走走,去迎一迎那些亲切的笑脸,感染似曾相识的气息。人还未从埕边的小路下行,一阵阵哗啦啦的水声就撞进耳朵,真应了河东先生笔下“隔篁竹,闻水声”的写照。这水声虽非“如鸣佩环”,但“心乐之”的感受却是如此相同。
循着水声来处探看,一团团白浪正从路边十几米处的山沟奔涌而下,牵出一道跃动的光,头也不回地往前跑去。安章的雨着实深情,让藏在岁月的记忆也情不自禁地被勾了出来,给异乡的客人重现一些纯真的遇见,增添怀想。
这山涧何处去?安章人都知道,它几乎都一头扎进了村尾的水池里。这水池向村口连着村中唯一的小溪,溪水西来,随雨水和季节涨落,经过溪中杂草的荡涤,一身清澈地扑向水池,和山涧水一道旋转出一池碧波。
许是雨接连而下,溪水拼命地往上蹿,溪中的杂草被拨向两边,泥沙俱下,一股脑儿地涌进水池,原先的青绿变浑浊,水面也快涨至与岸齐平。此时,水池边的水尾桥拱起高于岸的桥洞,任水灌入而不满,继而汩汩泄出。看来,古人之于石拱桥防涝功用的预见性建设在民间广为流传,堪称智慧。
若非暴雨连击,池水终年波澜不惊,映着池边树的倒影,照亮前来垂钓者的身姿。池中微微露出的假山和造景石也染上点绿,经过太阳的烘烤,干成线条和色块随意搭配的图案,只等着池水再次浸润,重绘一幅幅绿意盎然的画。
看着看着,我不禁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原来安章之水是天上赐到山中来的啊!
路上到处是夜雨的印记,和雨水温存过的泥路、青草与树木散发着乡间独特的甜蜜,脚下的路却提醒着我们得小心。
行至百米外的一个分岔路口,前路窄小的台阶不知何时已被修整,亮出一道道浅黄色的泥土,踩上去踏踏实实的。这里的村民真细心啊!
一转身的工夫,我们已经下到村道边的板栗树下。朝着村口走约一公里就是同事二伯的家,那是我们要寻访的第一站。眼前道路右侧是背靠小山的杨氏宗祠,一个弯月样的水池横陈于其前,得山水萦纡之景,别有意蕴。左侧是一连绿油油的田地,在秋风乍到还来不及吹开遍地金黄之际,农作物们纵情欢腾,涌动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海洋。
村道长长又弯弯,靠前的屋舍像统一了高度,顺着路排开,而后一排的则随山势往上攀升,似乎有山的倚靠就安稳了。这样的布局,让你置身其中时一眼无法望穿。最开眼的要数那阔气的稻田,从村头向村尾绵延。于是,村民们在田间约三分之二处设防,修几座房子拦一拦那奔涌的浪头。可它们从房子右侧的缺口处狡黠地拐个弯,又不管不顾地向前流去。在八月的安章里,这派风光实在养眼。
靠近田边瞧瞧,槟榔芋叶紧挨着路沿,盾形叶片或直立或开展。若是种上一大片,恐怕“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遐想就会不请自来。几丛茄子如灌木扎在田里,那垂在叶子下的又紫又弯的茄子油光发亮。若遇上绿色的长条茄子,你也不必惊叹,这里的人早司空见惯。在这个季节,田间也会立起几个架子,豇豆好长得欢。你看,那线形的荚果或缠绕或垂挂着,羽状复叶里还冒着一小簇黄白色而略带青紫的小花呢。还能占据一片天地的是生姜,它的茎挺起脊梁努力向上,可叶子就没有槟榔芋叶那么懂规矩,几乎都在顶上展开叶片,反倒是左右开弓地长出。秋风刚吹来,它们便忘乎所以地疯长。直至深秋降温时,它们才又乖乖地潜滋暗长。村民自然还会点些地瓜之类的农作物,不然干地与湿地的驾驭、时令与农作物的匹配,不就失去了平衡吗?田间之趣不也寡淡些许吗?
这时,你仔细想想,这种就势而为的生产生活之用,不仅有效地保护地容地貌,而且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直观写照。
顺着村道,我们很快到了同事的二伯家。老人连忙把我们迎进门去,招呼就座,烧水泡茶,原先的拘谨一扫而空,我随着同事也叫老人二伯。二伯的笑容如他家门前绽放的大丽菊那样灿烂,古铜色的脸上仿佛有光,眼中涌着山泉般的明亮。
二伯说,他早知我要来,又询问起吃住等等,关心着我们是否习惯乡下的生活。对于一个也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常居城市的成年生活正悄然掩盖了少时的印记,然而始终无法抹去成长的烙印。之于安章,陌生的感觉中又总渗着一股熟悉,况且又是面对着这样的二伯呢!
听同事说,为了我们的到来,二伯兄弟帮着他打理木屋埕上的杂草。半个月前,成堆的芦苇长到二楼高,一簇簇分散的则顽强地占地为王。它们挺着带绒毛的高高的秆,侧长的叶片狭长又锋利,一不小心就拉开一个个口子,单是靠锄头狠狠地掘,断是难以铲除的。他们只好拿着约两米长手柄的柴刀,像开路那样先砍伐一番,然后再喷洒除草剂。等芦苇的根被除草剂腐蚀七八天后,用锄头猛掘几下,几乎就可以斩草除根了。而收拾埕上六七十平方米的杂草,多年劳作的长辈们恐怕也得费上一番功夫吧。
快十一点时,二伯笑吟吟地说:“中午就在这里吃饭。”我赶紧找了个借口婉拒,准备向他道别。这时,二伯示意我们等一下,接着从旁边的巷子里提着一些东西出来,递给我。绿茄子、马铃薯、丝瓜和豇豆等菜蔬鼓起袋子,满满情意。我拉着孩子们向二伯道谢、作别,原路返回木屋。
回木屋后,我在厨房的柜子前铺上几个塑料袋,把那些菜蔬一一摆放好。紫红色的豇豆细长而深沉,绿色的丝瓜和茄子显得精神,而米黄色的马铃薯蒙着薄薄的土气,斑驳陆离,在厨房的黑土地板上自在地吐露心语。瞧着它们,我不禁想起来安章前,同事曾给的忠告,说是要等圩日赶集时,或到三十几里外的另一个镇方可买到菜,心里便不自觉地笑了。
泡一杯清茶,解解午饭的油腻。凭窗而坐,黄汤入喉,暖意盈盈,独立悠闲的时光。俄而,小门里踱进一个人来,他脚步轻盈,手提红袋子,满头的银丝把脸映得黝黑,透亮的眼神中分明扬着矍铄的状态。我起身应对,从言谈中方知,他便是那夜在双层木屋走廊上喊话的老人。
老人边翻开红袋子边介绍道,这些地瓜叶是刚采的,留着藤,等要吃的时候再摘掉,这样方便保存。我借机向他请教安章的信息,老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推荐我去拜访村中的一位退休教师。这时,他抬手看了下手表,说那位教师有午睡的习惯,如果我不忙的话,三点多可带我去。于是,我们就这样闲聊着,直至太阳渐渐西斜,日光松软。
沿路而下,至村道时左拐,行百余步就可见杨老师的家。他家的埕上摆着不少绿植,一颗高约四十厘米的蛋型鹅卵石居右侧,挺立在平坦的石板上,周边形态各异的小石块簇拥着它,错落有致地堆成一片假山的小天地,令人眼前一亮。一份遥想倏地在眼前浮现,退休后,我要择一方安章式的静地,莳花弄草,耕锄炊烟,安闲度日,好不惬意。
当我的想象还来不及深入时,杨老师已从卧室走了出来。我们在厅中落座,烟茶过后便进入正题。对于我的问题,杨老师胸中有丘壑,信手拈来,侃侃而答,还拿来《德化县志》《桂阳乡志》借我查阅。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让安章的前尘往事不断被勾连起来,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进宝山既已得宝,不如归去?我暗暗催促自己,打铁趁热,一回去就把它们记下来。正想着,杨老师却把我们邀到隔壁的小屋里去。小屋的木桌已备好土猪肉、咸菜干、苦菜汤,热气腾腾。一切顺势而动,吃菜,对酌,谈笑风生,至微醺。天色暗了下来,已是准备晚饭的时候了。想着孩子们在木屋里可能饥肠辘辘,而我又不胜酒力,只好在杨老师他们几位长辈的欢送下,带着歉意匆匆离去。
我刚走到去木屋小路中间的分岔口时,望见木屋的烟囱正徐徐地吐着白烟,烟气袅袅盘旋。我心中一阵窃喜。于是,我慢悠悠地进厨房,灶膛中的火苗却已熄灭,那些未燃尽的木炭正闪着红光。孩子们兴奋地告诉我,米饭煮好了。我掀开锅盖看,白白的米饭卧在锅里,品相甚好,居然没有一丝焦味。他们初次用大锅做柴火饭,就旗开得胜,不得不让人惊讶。
翌日,受二伯盛邀,我们去他家做客。餐桌上,一道鸡汤那般奶白,食之浓香清甜。于是,我便询问其中烹饪的秘密,从二伯口中方知得了茶油和柴火的加持。我接着追问茶油的腥味何以全然不在,二伯解释道,置茶油在锅中烧至将起泡沫时,撒少许盐巴,就可去味。看来,有时懂得老话比识字更管用。
记忆中,老家村后的山坡上曾有一片茶园,大人们就在其旁建屋做茶事。有时,我们几个小孩就钻进茶园里玩。茶园里,茶树一棵挨着一棵排成长条,一畦一畦地顺着山坡向下,油油的叶片密密匝匝的,泛着阳光的笑靥。在茶树下,我们曾摘过茶油果,它青铜色的外衣下包裹着一颗至三颗圆圆的内核。
掰开它的外壳,压碎内核,一种叫茶油的液体滑出,腥味随之而来。茶油原是不受我待见的,我曾因病抿过几小口,却受不住那味道而呕吐。后来,犬子调皮多磕磕碰碰,老人家提醒用茶油涂抹,说可以消肿化瘀,果见奇效。
吃饱喝足,我们便打道回小屋。临行前,二伯相赠茶油和散装的红酒,说都是自己做的,让我们尝尝。那黄澄澄的茶油、红馥馥的农家酒伴着我们,一路摇曳秋风。
秋风飒爽,撩动了茶油的思绪。从一株油茶苗到满枝的茶油果,寒来暑往,安章人秉锄躬耕。他们就地取材,木本合力,循古而做,汇聚天地精华和农人智慧的山茶油顺势而出,在锅里起舞,在人们的腹中蔓延,流动着秋天的欢愉和温暖。
等秋风凉到初冬时,油茶花就开了。在山坡上,在竹林边,一朵朵油茶花从油茶树的枝顶上或叶腋下露出脸来,洁白的花瓣如羽毛,薄薄的柔柔的,山风过处,盈盈而笑。花蕊矜持地立在正中,雄蕊细密繁多,鹅黄色的花丝上顶着黄褐色的冠;雌蕊被包裹在其中,越出的花柱在顶端浅浅裂开。
冬日的安章微寒,地里的作物又换了一茬。种点芥菜吧,来了霜冻时,它们在叶片的边缘卷起点焦黄,薄薄的晶莹蒙在叶面上,这些芥菜将更鲜甜。偶有小雪来访时,安章人古时的火笼就派上用场,灶头的木炭余温在火笼中酝酿着,双手一捂,热气就蹿到身上来。来点日光时,他们就着门前的长木板扎堆而坐,谈天说地,融融洽洽,也欣欣然。
这样的时光悠闲,安章人却一点儿也不懒散,他们知道要采茶油果了。立冬将至,大部分茶油果旧貌换新颜,如同饱经了风霜,原先青色也成青铜色,露出成熟的面孔。而有些茶油果禁不住风吹雨打或自己实在忍不住,便嗒嗒地掉落在茶树下,等待种茶人来拾去。
世间的收获并非如想象来得那般容易。在茶油果渐渐拉低茶树枝条的夏日里,佳木秀而繁荫。油茶树四处捕捉阳光,越发青绿。瞧,叶片们忙着呼吸,闪动着片片光滑的亮光,在树下,杂草们似乎因了油茶树的荫庇,遍地葱茏,是到除草的时候了。
这时,安章人搭着锄头,提着小锅,带点菜,不约而同地来到山坡上。茶园里的劳作琐细,往往非半日可就。中午停歇时,信手拾些木柴,就地掘个小土灶,小锅往上一架,生火,干柴烈火的时间烹制出米香。配上点自制的笋干、咸菜之类的菜肴,一顿简易便捷的午餐赓续了劳动的活力。一年下来,熬到茶油果收成的时节,免不了忙忙碌碌好几回。
虽是如此,终还是有些茶油果跋涉不到寒冬,被秋风早早扫去,被孩童当作玩耍的物件,被鸟儿啄落,遗弃在某个地方,乃至枯槁、腐朽,复归于尘土。而那些被摘的、被捡的茶油果是幸运的,人们用巧手和智慧,帮助它们实现了金黄色的梦想。
太阳大些时,将茶油果在大簸箕上铺平,晒上数日。被阳光热吻过的茶油果,有的不解风情地缩成一小团,人们便在闲暇之余动手剥开它们,取出茶籽。许多则是乐开了花,裂开果壳,露出浅褐色或黑色的茶籽,一些肥嘟嘟的微黄色虫子也趁机蠕行至簸箕周边。这些茶油果的窃食者,人们把它们变害为宝,抓在一起干煸,抓一小把扔进嘴里嚼嚼,香味十足,蛋白质满满,口感胜似爆米花的爽脆。
大茶油果硕大如青皮梨,小茶油果小巧似鹌鹑蛋。它们内含的茶籽不同,色泽不同,出油率也不同,所以得各自归置。等茶籽们被一网打尽后,得再被送去做个日光浴,消去水分,换个结实的身板后,被送到石碾坊里,等待生命的新一轮觉醒。
眼前的露天石碾坊,是由鹅卵石铺就的大圆,约三四十平方米,由数个圆和两根木棍组成。一个圆形的凹槽当圆心,在其上立一根一米左右的短木。取一块青草石雕成圆磨盘,挖出圆心,将边沿打磨成较薄的刃口。在大圆的边上筑一个沟槽,安放石磨,寻一根二三米长的横木,连接石磨和短木,一头插入石磨的圆心,另一头扎进短木上打的孔,固定成劳作的姿势。接着,沿着沟槽撒上茶籽,石磨在外力鼓动下打圈。被碾过的茶籽吱吱作响,铲子紧随其后,唰唰地翻,下而上,上而下,循环往复。
被碾碎的茶籽填满大木桶,放在煮水的锅中,感受木柴的炽热,这是蒸茶籽。等茶籽被蒸透,做茶饼的师傅就出现了。他们将一个或两个铁箍叠在一起,一小捆稻草放置其中,放入被碾好的菜籽,压实再压实。在你还来不及看仔细时,他们信手一拨一揽一搓,一个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圆形茶饼已成。做好的茶饼码在一起,肩挑或用车运至制茶油的作坊。
说是作坊,其实简易得很,最大的道具是一截数米长、几近被掏空的树干。他们将这树干掏出一个长长的木槽,在木槽底部的侧方开个小孔。一个个茶饼并排而立,直至无法加入。此时,榨茶油的师傅会开始在木槽的顶部加塞木块,直至将茶饼们的空间压榨到无以复加。
打开已凿好的小孔,金色柔软的茶油便酥酥地滑入桶中。
【作者简介:李锦秋,80后,福建晋江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光明日报》《福建文学》《诗歌月刊》《散文百家》等。出版散文集《平静地收获》《时光未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