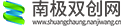本文刊2011年5月29日文汇报·笔会,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于当年5月5日在“大江健三郎文学专题研讨会·东京”上发表的演讲,由许金龙先生翻译。
如大江在讲演中所说,这个研讨会是在他“长达五十四年的作家生涯中,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是第一次以我为中心主题而召开的会议”,更是在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泄漏大事故这一连串天灾人祸的特殊时期召开的会议。这就使得大江先生在演讲中不可避免地审视这种特殊状态,审视产生于两次巨大危机之间的自己的文学和日本人之未来……
1.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今天的专题研讨会,在我长达五十四年的作家生涯中,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是第一次以我为中心主题而召开的会议。我至今仍然在写着作品,我在想,因为过于长久、持续地一直在写着小说,“过去的作家”这个评价该不会已然固化了吧?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的二儿子正在做高考前的准备,在补习学校的一个班级里,有个“当代日本文学”讲座,我便去了那里,一位听讲者好像对教师发下的讲义提出了异议:“讲义里列有大江健三郎这个条目,可是大江恐怕不是当代文学,而是属于现代文学吧?”
进入大学之后,二儿子热衷于越野识途竞赛活动,在电话里与朋友商议为参加比赛而去外地等事宜时,经常会这样说道:“稍等一下,我要得到我家那位现代文学的同意。”
不过,作家只要还活着,就不可能与其时的社会毫无关联。然而,我这么一个作家能够成为2011年在这个国家召开的国际性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吗?而且,我们的国家,目前正面临自明治的现代化进程以来的、恐怕是第二次遭遇到的最大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太平洋战争的战败以及其后的复兴期。那是在世界上首次被核武器制造出来的废墟之上为复兴而努力的时期。
当然,也存在着一种说法,那就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与东京大空袭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是,作为日本现代史的危机,我却是以核武器为轴线,来思考1945年和紧随其后的危机,并将福岛核电站的巨大事故置于当下这场危机的焦点之上。在这两次危机之间,日本渔民因比基尼环礁的氢弹试验而遭受了核辐射。
来自于中国和韩国的、多年来为我所敬爱的朋友们参加这场专题研讨会,使我抱有深切的感激之情。但是,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人,在北京或是在首尔,肯定会被问及“为什么现在要前往放射性污染之源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八个星期,却仍然未能制定出根本性对策,围绕福岛核电站的这种状况,我是洞察性地将东日本至东京之间的距离看得非常遥远呢?还是想象着不久后两地将成为同一块被放射性所污染的区域?抑或站在前一种认识和后一种想象力的其中一方?我认为,这关乎从现在走向将来的日本人之选择。面对与会代表,我的沉痛何止两重三重之深?!
我处于这样一个位置——自己是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或是素材,只是听听大家的发言即可。可是随着会期的临近,我也不得不思考自己是作为怎样的作家度过这漫长岁月的。当我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如此大规模研讨会之主题系、即thématique的内容时,却感觉到了阵阵不安。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
在像是持续不止的巨大余震中睁开睡眼仰望黑暗并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弄清楚的单纯事实,便是一如刚才对大家讲述的那样,是在两个巨大危机之间生活过来的人生,是如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其结果,就是我总是处身于“危险的感觉”,睁大眼睛竖起双耳一般生活至今,我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危险的感觉”源自W·H·奥登的诗句“The sense of danger must not disappear”,这是我借以把握从青春期至壮年期的话语。在我从壮年期至老年期的这段时期,T·S·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之后的诗句则发挥了同样作用。
我想要结合这一点告诉大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时所做的评价中,有一句用英语表述的“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或许是在当地的日本大使馆的介入下,这句话被翻译为“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真实状况’”这句日文。大致说来,恐怕不存在不去描述同时代人真实状况的小说吧。如此说来,这句话语便是同义重复了。“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这个英语句子里确实含有“某种状态、境遇”等中性语义,然而我愿意在更为普通的语义上将其对应于困境、窘境、绝境。我的小说从最初起步直至将近终点的现在,始终在描述一个日本人所经历和想象的困境、窘境、绝境,那是因为我所生活和描述的正是处于这两次巨大危机之间的时代。
2.
不过,将自己的文学仅仅定义成对predicament·窘境进行的描述,则不足以构成一场专题研讨会的主题系,因而我现在便面临着一个新的窘境,那就是由自己将这个主题系分解为若干主题,从而为这场专题研讨会做好心理准备。首先需要确定文学的技巧,也就是小说的叙事方法,设定出与作者本人多有重叠的主人公,让其在文本中进行叙述,在若干长篇小说中将这位主人公的叙事连接起来,这种技巧(在不得不称之为晚年的自己这十多年间,我在小说里一直专注地使用着这种技巧)果真能够经得起专题研讨会的讨论吗?
如此这般地想到这里,虚拟的信心便开始产生动摇。而且,在以国家规模如此迫近的巨大危机中,这种讲述能否满足前来垂听的听众们的迫切关心?
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尽管我也觉察到在研讨会之前便谈及会议论文内容有违反规则之嫌,却还是要指出,沼野充义先生的立论让我感受到了鼓舞,这个立论恰好印证了刚才所说的、有关小说技巧的主题,而且兼顾了正面临着眼前这场危机的这一问题设定。我期盼着在这个会场亲耳聆听这篇论文。
为什么我会了解到这些情况呢?因为三天前,我收到了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所有代表的讲演稿,而我本人则写得最晚,大家由此便可以推察出我所陷入的窘境。
我兴奋地连续阅读着所有讲演稿。以陈众议先生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论文内容充实,再度表现出曾于大陆和台湾两地召开的研讨会(我出席了这两场会议)上切实显示的那种明快的展开。为配合耗费时日准备的这场专题研讨会的会期,以许金龙先生惊人的努力为核心,中方代表的论文所涉及的我的所有作品均被翻译成了中文。迄今为止,我参加过广泛涉及各种主题系的国际专题研讨会,却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之彻底的会议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论文,均自然地扎根于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使我从中受益良多。在我如此兴致勃勃地阅读这十二篇论文之际,内人难得地生发出好奇心,尤其当她读完韩国和(日本)这个国家的女性代表的论文后,也不禁为之而感动。内人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我们结婚五十多年了,她一旦开口说起话来,便往往会说出让我意想不到的话语:“如此精挑细选的女性们为你所作的这些发言,估计不会再有了吧,因此呀,你不妨看作自己的生前葬礼。”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所谓生前葬礼,就是在尚且存活期间,考虑到原本就并不遥远的死亡,由本人预先举办的葬礼。
沼野先生在刚才提及的论文中指出,大江最近的小说虽然与日本特有的文类“私小说”有相似之处,却是包含着全然不同之质感的Metonymy,已然从家庭的实际生活稍稍错开,即便相同于实际生活,那也是正常的Metonymy般的存在。所谓Metonymy,是比喻的一种形式,我认为这种Metonymy相对于直喻和暗喻,是文学里最为有趣的技巧,可以将其翻译为换喻或是转喻。不过,在非小说领域,我可没有勇气使用Metonymy形式讲述有关内人的话语。刚才的发言,便是基于“私小说”原则而原样讲述的事实了。
一如我于刚开始时讲述的那样,目前我在写着自己的“晚年的小说”(这便是我的多年老友爱德华·W·萨义德所说的late style),正在这部小说里写着自己从不曾写过的祖父。这个人物在少年时期分别参加了爆发于万延年间以及其后数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即便被他们如此抵抗的权利机构倒台、明治新时代开始以后,他也绝不信任明治政府,长年间潜藏在自家房屋的地下仓库里。年届五十后,他走上地面并结了婚,有了我的父亲。我家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老人在临死之前,复活了森林中的民间传说——制作了用树皮和枯叶缝制而成的死亡装束,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
我们将在后面的研讨会上亲耳聆听让内人心生感激之情的这三位女性出席者的演讲,我只想就其中最年轻的朝吹真理子君说上几句老年作家预言般的话语(倘若是生前葬礼的话,就该算是遗言了)。这位新作家目前广受瞩目,在她的作品里,我时常发现镶嵌于其中的若干“有力量的话语”。人们会屡屡说起“纤细的话语”和“感性且锐利的话语”,可是“有力量的话语”却是伴随着独特的作家终生的、命运一般的话语。
3.
刚才我说到自己年轻时曾受到奥登的强烈影响,从壮年期至老年期,则置身于艾略特那相同的回响之中。现在,仅仅如此提及这个名字,艾略特的一节诗歌便开始鸣响于我的内心,我在小说里也曾引用过这节诗,那是他晚年间创作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一部分:
And what the dead had no speech for, when living,
They can tell you, being dea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dead is tongued with the fire beyond the language of the living.
有人在这场研讨会的论文中亦指出,我对于外文诗歌的阅读方法,首先是记忆原诗,然后便同样记下自以为最优秀的那首诗歌的日文译文。在眼前这个场合,则是西胁顺三郎的译文:
死者们在生前
无法言说的话语
死去之时却可以向人们讲述。
死者们的传达
超越生者们的语言,用火
表明。
西胁围绕艾略特的这节诗所作的翻译,对我来说极为重要,这种重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Communication这个单词以其独有的深度和强度,镌刻在阅读了原诗的我本人的精神上。而且,这个英语单词是因着我配套阅读的西胁译文,而与“传达”这个日语单词重叠起来,一同在我的身心镌刻下痕迹的。在我如此背诵艾略特的这首原诗之际,“Communication=传达”这一对单词也因此而在我的精神和身体上站立起来。
去年四月,我长年以来的朋友、剧作家井上厦先生去世了。在他故去之后,夫人将他的两册笔记送给我,其中的文章显示出,大致同年出生的井上先生果然在用火表明他与我之间那种同时代的批评关系(在这种场合,是从他的笔记中单向地对我进行传达)。
二十五岁的井上先生在评论我最初创作的短篇小说时,表示我的作品以“人生的平行=与他人无涉”作为主题是出色的,但是在对我的短篇小说表示认可后,他接下去便如此写道:
我在担心,大江氏恐怕难以写出出色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长篇小说这一领域,除了描绘爱之外便写不出其他东西来。归根结底,大江氏是个短篇小说作家。
也是在二十五岁这个年龄上,我与一位敬之爱之的友人的妹妹结了婚,由于我生性便对重复相同之事感到厌倦,就从不曾重新爱上其他女性。如此一来,也就无法基于体验而写作罗曼传奇、也就是有关爱的长篇小说了。井上厦先生的预言说中了!然而,如同总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等候着我一般,predicament·窘境很快便来到我的面前——我成了一个智障儿的父亲。就这样,新的爱来到了我的身上。我的长子在始于《个人的体验》的诸多作品里被称为阿亮,我以自己与长子的共同生活为主题而创作长篇小说,井上先生在其后的人生中对这一切给予了好评。
不过,依然在这同一主题系内、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被更为集中地论述的长篇小说《水死》中,我描述了阿亮与父亲的不和,最终在小说临近结束处,描绘了两者间的和解。井上先生在临终的病床上阅读了这些描述,在遗留下的笔记上洞察性地指出我与长子的和解是虚假的:“压倒性的阿亮君之存在,除了真正充满人性的事物以外,则不可能达成和解。”
井上厦先生在用火表明基于他与我之间终生相互理解的、却是绝不妥协的批评之传达,将生者们绝不会说出的话语传送给了我。作为对他的回应,目前我正写着恐怕是The last work的“晚年的小说”。大家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对《水死》所作的多方面探讨,将会坚实地推动我的这一工作。
在我的人生中,Predicament对我的造访从不曾间断,尽管有时会隔上一段时间。不过,同样近似不可思议的幸运的理解关系也不时惠顾于我。我接近人生终点之际的、显然是最大的幸运之一,便是为我策划、准备和实现了这场专题研讨会的友人们以及光临研讨会的诸位,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年5月5日,于东京
作者:大江健三郎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